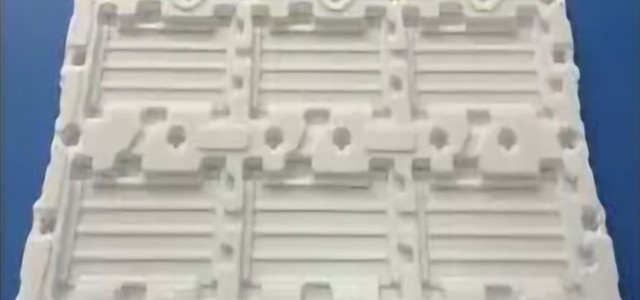2021年7月13日,北京大學(xué)2021年本科生畢業(yè)典禮暨學(xué)位授予儀式。 (視覺中國/圖)
張繼平有兩個最主要的身份,做研究的數(shù)學(xué)家和教數(shù)學(xué)的老師。
1982年本科畢業(yè)考上北京大學(xué)數(shù)學(xué)系后,張繼平師從中國群表示論奠基人段學(xué)復(fù)院士,投身有限群領(lǐng)域的研究,29歲時解決布勞爾39問題。32歲成為北大最年輕的教授、博導(dǎo)之一,40歲出任北大數(shù)學(xué)科學(xué)學(xué)院院長,49歲時開辟有限群與模表示論研究的新方向,50歲獲得陳省身數(shù)學(xué)獎,61歲當選中國科學(xué)院院士。如今,張繼平還擔任北大中俄數(shù)學(xué)研究中心和南方科技大學(xué)杰曼諾夫數(shù)學(xué)中心主任。
他的教師生涯卻是從語文開始的。高中畢業(yè)后,張繼平在山東成武縣一所小學(xué)當語文老師。1977年恢復(fù)高考后考入山東大學(xué)數(shù)學(xué)系,自此,詩歌與韻腳變成了等式與數(shù)字。從小學(xué)語文老師,到大學(xué)數(shù)學(xué)老師,張繼平回溯過往時提到,“一個好的數(shù)學(xué)教師,首先必須是一個好的數(shù)學(xué)家,而一個好的數(shù)學(xué)家應(yīng)該肯花精力在培養(yǎng)新一代數(shù)學(xué)家上。”
某種意義上,張繼平已經(jīng)培養(yǎng)出了新一代數(shù)學(xué)家。2021年4月,因為一篇《在北大數(shù)院,成為一個普通人》,號稱“中國第一系”的北大數(shù)學(xué)系進入大眾視線。在北大數(shù)學(xué)系培養(yǎng)的諸多學(xué)生當中,“黃金一代”又是最耀眼的代表,他們集中在2000年前后入學(xué),三十多歲在國際數(shù)學(xué)界取得了突出的成績。在“黃金一代”的求學(xué)過程中,時任數(shù)學(xué)科學(xué)學(xué)院院長的張繼平,領(lǐng)導(dǎo)制定了北京大學(xué)建設(shè)世界一流數(shù)學(xué)學(xué)科的規(guī)劃及其實施方案,計劃用10-15年的時間建成具有重要影響的一流的國際數(shù)學(xué)中心。
這個規(guī)劃和一系列改革舉措,也被視作北大數(shù)學(xué)發(fā)展及“黃金一代”成才的重要推力。
2021年7月下旬,在南方科技大學(xué)杰曼諾夫數(shù)學(xué)中心,張繼平接受了南方周末記者的專訪。
張繼平。 (受訪者供圖/圖)
人類社會越發(fā)展,越需要數(shù)學(xué)
南方周末:在考入山東大學(xué)數(shù)學(xué)系之前,數(shù)學(xué)和你的生活有交集嗎?
張繼平:沒有,之前從沒想過要從事數(shù)學(xué)研究,讀中學(xué)時甚至沒看到過一本真正的數(shù)學(xué)專業(yè)書。僅有一次回家,我爺爺不知道從哪找到一本上海科學(xué)出版社出版的《高等數(shù)學(xué)》,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與高等數(shù)學(xué)相關(guān)的東西。但我也一直喜歡學(xué)習(xí)數(shù)學(xué),中學(xué)時數(shù)學(xué)課學(xué)得也不錯,做過數(shù)學(xué)課代表。恢復(fù)高考那一年,我本來想報北大數(shù)學(xué)系,但1977年別的學(xué)校數(shù)學(xué)、哲學(xué)專業(yè)都招生,北大數(shù)學(xué)不招生,還沒恢復(fù)過來。后來我被山東大學(xué)數(shù)學(xué)系錄取。
數(shù)學(xué)是一門演繹的學(xué)問,是科學(xué)的語言。數(shù)學(xué)研究從絕對的、終極的和最基本的條件出發(fā),通過嚴格的邏輯推理,演繹歸納出結(jié)論,放之四海而皆準。所以說,人類社會越發(fā)展,科技越進步,就越需要數(shù)學(xué)。
南方周末:聽說1992年你在巴黎訪學(xué)時,離埃菲爾鐵塔非常近,卻沒去過,為什么?
張繼平:不止是埃菲爾鐵塔,巴黎圣母院、盧浮宮(也沒去),在巴黎時,我的生活全部被兩個數(shù)學(xué)問題占據(jù)了,一個是可解群的S3-猜想,另一個是Puig問題。一早起床,趕往巴黎高師的辦公室、圖書館,沒有時間想其他的,也不會想其他的。可能有很多人聽到這個就會覺得這人好苦,其實不是的,在數(shù)學(xué)研究的時候,數(shù)學(xué)家是很充實的,在取得研究進展的時候都是很享受的。這與怕辣的人看川人吃麻辣香鍋是一樣的。在巴黎高師一年多,我解決了上述第一個問題,第二個問題取得決定性進展,今天回憶起來仍感高興和幸福。巴黎訪問結(jié)束后,我到德國開始洪堡高級研究員的研究計劃。幾年后我多次到巴黎、馬賽等地訪學(xué),見了不少景觀,那些具有悠久歷史、歷經(jīng)風(fēng)雨的建筑和景物仍能以原物呈現(xiàn),令人感慨。
南方周末:作為數(shù)學(xué)家,你的一些理論突破是別人十幾年甚至三十幾年都沒有解決的,你有沒有思考過,能夠?qū)崿F(xiàn)理論突破的數(shù)學(xué)家身上有哪些共性?
張繼平:實際上這些問題不止一個人在研究,就像很多人研究短跑比賽誰能得第一名,其實這是各方面因素綜合影響的結(jié)果,可能換個環(huán)境,冠軍人選也不同了。
此外也有很多其他因素,有的人會用一輩子的時間去解決某個問題,日積月累才能得到結(jié)果,不可能一拍腦袋就想出來。
安德魯·懷爾斯從1986年開始研究費馬大定理,我在北京接待他,他和我聊天中說起,就是直覺。他認為好多前人都走到了這個地方,已經(jīng)做好了充分準備,解決問題的時機到了,這次絕不能讓這條大魚跑了,之后他進行了7年研究,到1993年收獲成果。但在一開始,并沒有多少人能準確認識到已經(jīng)可以集中精力去研究了。我當時就問他,您是怎么精準地選擇了這個問題,他和我說,“the problems choose me(是問題選擇了我)”,雖然這話聽起來有點吹牛的意思,可是我覺得他有這個自信,也有一定道理。畢竟天底下就他一個人解決了這個問題,當然選的是他。數(shù)學(xué)問題的解決大多類似,不過沒他這么有名罷了。
不能用流水線方式培養(yǎng)一流人才
南方周末:除了數(shù)學(xué)家身份,近些年你進入大眾視野,多半是以北大數(shù)院前院長的身份,外界對你的了解,似乎更多來自對“黃金一代”的培養(yǎng)。
張繼平:對二十幾歲的年輕人來講,能知道北大這個前院長的人也不多。“黃金一代”的故事從1999年開始,在1999—2001年入學(xué)的這三屆學(xué)生中,北大陸續(xù)走出七八位優(yōu)秀的青年數(shù)學(xué)家。
后來在2010年被《中國科學(xué)報》報道出來,最開始接受采訪的是華人數(shù)學(xué)家、普林斯頓大學(xué)教授張壽武,他起了“黃金一代”這個名字,那時北大沒人接受采訪,我更沒有講過任何培養(yǎng)經(jīng)驗。又過了10年,“黃金一代”成了叱咤風(fēng)云的人物,我也沒有提過此事。
“黃金一代”這四個字所產(chǎn)生的光芒,是因為他們的工作重要。他們是需要大家關(guān)注,要學(xué)習(xí)他們發(fā)展的理論和方法,至于我們這些曾經(jīng)做了一點工作的人,也需要腳踏實地,做更多事情。而且我對他們寄予了更大希望,不只是走到世界最前沿,做出最好的研究,要給中華民族爭光,這是我心心念念的。
南方周末:對大眾來講,像“黃金一代”這批數(shù)學(xué)家取得的成績,也會幫助理解我國目前在數(shù)學(xué)領(lǐng)域的發(fā)展階段和前景。
張繼平:有這方面的影響,但我非常清楚,雖然我們有了“黃金一代”,但不意味著什么都是黃金。
像惲之瑋、張偉、朱歆文、袁新意、劉若川、許晨陽、劉一峰、肖良等“黃金一代”,都是在北大讀的本科,但沒有一個人的博士是在國內(nèi)讀的,從這一點來看,我們和國外是有差距的,還需要沉下心來提高人才培養(yǎng)的質(zhì)量和水平。當然,隨著這些年國內(nèi)數(shù)學(xué)研究和數(shù)學(xué)教育的發(fā)展,完全由我們自己培養(yǎng)的數(shù)學(xué)家也已經(jīng)走到了世界頂端。明年的世界數(shù)學(xué)大會,國內(nèi)大概有12位數(shù)學(xué)家受邀作報告,北大就有5個,其中朱小華和章志飛完全是國內(nèi)培養(yǎng)和成長起來的,現(xiàn)在人才培養(yǎng)的質(zhì)量已經(jīng)在彌補“黃金一代”的遺憾。
2017年12月3日,有“科學(xué)界奧斯卡”美譽的科學(xué)突破獎頒獎典禮舉行,數(shù)學(xué)家惲之瑋和張偉獲得“數(shù)學(xué)新視野獎”,兩人是北大數(shù)學(xué)系2000級的本科同學(xué)。 (視覺中國/圖)
南方周末:這樣一批頂級數(shù)學(xué)家集中涌現(xiàn),你任院長時有沒有預(yù)見到他們未來的成就?
張繼平:我們當年還真沒有像今天這樣的明星班、尖子班、精英班,腦子里想的都是全國各地的尖子生匯集到北京,在北大、清華,應(yīng)該再怎樣去選拔、培養(yǎng),讓有潛力的同學(xué)成長得更快。
畢竟學(xué)生與學(xué)生還是有差別,擅長的方面不同,需要在整體的平等條件下給予個人選擇的空間,所以從1999年開始,我們設(shè)置了低年級討論班,每位同學(xué)都可以報名,由我和副院長鄭志明院士分帶兩個班。當時數(shù)學(xué)科學(xué)學(xué)院一年招生200人,我和鄭院士根據(jù)學(xué)生的特長,從中選出60個人左右,每個班30個人左右,每周上一兩次課,教授課外的拓展知識,帶領(lǐng)學(xué)生們閱讀一些有科普性、思想性的論文或著作,當然,最主要的數(shù)學(xué)理論還是留在面向全體學(xué)生的課內(nèi)講授。“黃金一代”這批人,都是從低年級討論班中走出來的。
我們就是根據(jù)學(xué)生的興趣愛好和特殊需求,來進行一些因材施教。這方面,孔老夫子有教無類、因材施教的思想是我們培養(yǎng)出類拔萃學(xué)生最根本的指導(dǎo)原則,用工廠流水線的方式培養(yǎng)一流人才是不行的。
但現(xiàn)在也面臨著另一個問題,大家非常關(guān)心教育公平,大學(xué)錄取率從1977年時的5%,到現(xiàn)在已經(jīng)超過85%,從精英化向大眾化轉(zhuǎn)變,考試難度、教材難度都在減小。很多家長和老師反映,現(xiàn)在的大學(xué)入學(xué)考試喪失了選拔拔尖人才的功能,影響了拔尖人才培養(yǎng)。因此在高等教育向大眾化轉(zhuǎn)變、培養(yǎng)高素質(zhì)勞動者的同時,我們可能也需要花費更多精力,認真做人才的選拔工作,特別是數(shù)學(xué)家要積極參與到拔尖人才的選拔和培養(yǎng)當中去。
南方周末:你有沒有思考過,國內(nèi)的數(shù)學(xué)研究或人才培養(yǎng),和國外相比差距在哪里?
張繼平:這是一個大問題。在培養(yǎng)數(shù)學(xué)家、使得大家集中精力搞學(xué)問方面,國內(nèi)的整體環(huán)境還需要改善,當下功利浮躁的氛圍還是要進一步克服;從歷史發(fā)展看,理性、科學(xué)的思維一直缺少一點,想長遠地進行科學(xué)研究,還是需要沉下心來做學(xué)術(shù)。懷爾斯在普林斯頓大學(xué)任教期間,7年基本沒發(fā)表過文章,專心研究費馬大定理,可是外邊的人不知道。這種情況下,單位能不能允許他這樣做就成了一個很重要的因素。當然,就算是懷爾斯這樣的大數(shù)學(xué)家,大家知道他是不會浪費光陰的,但數(shù)學(xué)研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,難以預(yù)料,的確有一定風(fēng)險,有風(fēng)險才有機遇,世界才能發(fā)展。
南方周末:你任北大數(shù)院院長時曾提出,不能單純用論文發(fā)表量去衡量學(xué)者的科研能力,但直到最近,討論熱烈的還是用論文發(fā)表量、教學(xué)時長去考評高校教師的問題。
張繼平:這件事情確實很重要,也是現(xiàn)在困擾很多青年人成長的問題。現(xiàn)在很多單位難以評價一個數(shù)學(xué)成果的重要性,看在核心期刊發(fā)表過文章,就覺得他很厲害。可能也不見得。解決這個問題還是需要在體制機制上下功夫。就北大來講,我們堅決反對唯SCI文章是從。我當了兩屆院長,沒有哪位老師因為沒發(fā)表什么類型的論文受罰。每年我們都會填一個表,讓各位老師總結(jié)這一年的工作和成果,比如教學(xué)、科研、社會服務(wù),發(fā)表的文章和想法,但這主要是學(xué)院整體工作的統(tǒng)計匯報。在學(xué)院能控制的范圍內(nèi)給予老師一定的自由。
當然,在大的社會環(huán)境下,老師也不可能完全脫離,評職稱學(xué)校有一定的標準。我任院長時,采取的方式是增加數(shù)學(xué)科學(xué)學(xué)院學(xué)術(shù)委員會在學(xué)校的話語權(quán),希望學(xué)校盡量尊重學(xué)科的意見,所以會出現(xiàn)我們內(nèi)部認為某位學(xué)者達到了教授水準,但按照量化指標,他又不符合要求的情況,這時候就需要力爭破格。當然這個“格”不能隨意破,也不能經(jīng)常破。其實這些辦法和做法沒有多高明,只是希望由數(shù)學(xué)家來為數(shù)學(xué)家做出專業(yè)評價。
數(shù)學(xué)成績?nèi)〉么蠖嘣?0歲之前
南方周末:之前有一篇《在北大數(shù)院成為一個普通人》,提到北大數(shù)院很多學(xué)生可能都是高分考進去的,但入學(xué)后逐漸發(fā)現(xiàn)自己跟不上,或者與別人還存在很大差距,你怎么看這種情況?
張繼平:是要有普通人的心態(tài)。我們的教育應(yīng)該讓學(xué)生努力成為一個普通人,特殊只是因為你有一些特殊的才能。
我問過一個世界著名的數(shù)學(xué)家,現(xiàn)在也是中科院院士,我說你那么小就展露出杰出的數(shù)學(xué)天賦,為什么拒絕去少年班這樣的班級學(xué)習(xí),他就說自己不愿意被貼標簽,愿意和同齡人快樂地生活在一起。
在大學(xué),盡管每個人都不一樣,但大家聚到一起可以各取所長,學(xué)校層面也要給大家創(chuàng)造這種機會,互相學(xué)習(xí),而不要封閉起來,或者給學(xué)生貼標簽,讓他覺得自己有多厲害,樣樣都要比別人強,無形中增加心理壓力。
南方周末:那大學(xué)培養(yǎng)數(shù)學(xué)系學(xué)生,最終的目標是什么?
張繼平:我們有很多學(xué)生對數(shù)學(xué)有興趣,但并不是十分了解數(shù)學(xué),有興趣當然很好,這是學(xué)好數(shù)學(xué)的一個重要條件,至于要不要、能不能成為一個職業(yè)數(shù)學(xué)家,又是另外一回事。
當前數(shù)學(xué)理論越來越深刻,應(yīng)用越來越廣泛,大多學(xué)數(shù)學(xué)的大學(xué)生都不是為了成為數(shù)學(xué)家,而應(yīng)該用所學(xué)的數(shù)學(xué)知識在其他領(lǐng)域做出更多探索,例如金融、保險、經(jīng)濟、工程、信息等領(lǐng)域。很多交叉學(xué)科都是以數(shù)學(xué)為基礎(chǔ),已經(jīng)成為科學(xué)發(fā)展的一種趨勢,如果數(shù)學(xué)系的學(xué)生將自己的數(shù)學(xué)之長運用到其他領(lǐng)域,可能會比在數(shù)學(xué)研究方面更有前途,發(fā)揮的作用更大。
從另一個方面來看,可能也不需要太多專門研究數(shù)學(xué)的人,畢竟對數(shù)學(xué)感興趣和研究數(shù)學(xué)還是不同的。
2021年7月21日,北京,“凝心聚力跟黨走——首都職工慶祝成立100周年綜合展”上,張繼平的半身像。 (視覺中國/圖)
南方周末:數(shù)學(xué)界的最高獎項菲爾茲獎,年齡要求是40歲以下,而其他如諾貝爾獎對科學(xué)家并沒有這一項要求,為什么數(shù)學(xué)這么特殊?
張繼平:數(shù)學(xué)是年輕人的學(xué)問,是思維的體操,是人類智力的考驗,不是說世界上的數(shù)學(xué)家都瘋了才設(shè)立這樣一個界限,而是驚天動地的數(shù)學(xué)成績的取得,大多在40歲這個年齡之前。
當然也有數(shù)學(xué)家在40歲之后才取得很高成就,只是總體來看,數(shù)學(xué)一直就是年輕人的學(xué)問,二三十歲是關(guān)鍵,這是這個學(xué)科的特點所決定的。物理學(xué)家、化學(xué)家都可以依靠實驗手段,唯獨數(shù)學(xué)只是高強度的智力競賽,就像百米沖刺時運動員的爆發(fā),數(shù)學(xué)研究一定要有創(chuàng)造性思維的爆發(fā)。
我過了45歲以后,想一鼓作氣,連續(xù)工作十幾個小時不休息,已經(jīng)做不到了。二十幾歲時,我只要有一個想法,可以一天不休息,就是要把它寫出來,困了打個盹、喝口水就行,現(xiàn)在一旦打盹,就睡幾個小時才行,這是自然規(guī)律,就算再聰明,過了那個階段,那種爆發(fā)的力量已經(jīng)沒了。
南方周末:按照這樣的時間要求,比起其他學(xué)科,數(shù)學(xué)人才培養(yǎng)的周期和要求是不是也要有相應(yīng)的調(diào)整和改變?
張繼平:需要給更多年輕人創(chuàng)造機會。雖然我們現(xiàn)在的一些措施是在給人才創(chuàng)造機遇,但另一方面,年齡較大的數(shù)學(xué)家怎么繼續(xù)發(fā)揮創(chuàng)造性的問題,一直以來也是爭論不休。雖然數(shù)學(xué)是年輕人的學(xué)問,但每個人都可以延長自己的數(shù)學(xué)壽命。像張益唐58歲破解了世界難題,現(xiàn)在66歲還在攻克更大的問題。
南方周末:你現(xiàn)在任中俄數(shù)學(xué)研究中心主任,也在主持南科大杰曼諾夫數(shù)學(xué)中心,在中外學(xué)術(shù)交流過程中,你覺得未來國內(nèi)的數(shù)學(xué)教育和研究要朝向哪個方向發(fā)展?
張繼平:我們應(yīng)該從過去的跟蹤向引領(lǐng)世界數(shù)學(xué)的方向發(fā)展,建立更多前沿學(xué)派,不僅是要去證明一個個定理,而是要建立一門學(xué)問。雖然這件事很難,但還是要朝著這個方向前進。今后的四五十年,中國的數(shù)學(xué)發(fā)展應(yīng)該更多關(guān)注到國際前沿學(xué)派的建設(shè),盡最大努力實現(xiàn)數(shù)學(xué)理論的重大突破,所以國際交流是我們非常關(guān)注的事,要按科學(xué)規(guī)律和國際規(guī)則辦事。但我們離真正的國際化還有一段路要走,未來應(yīng)該在國際化方面多發(fā)揮偉大科學(xué)家的作用,無論國內(nèi)的還是國外的,過去我們總是向別人學(xué)習(xí),也是時候形成有自己特色的東西了。
南方周末教育頻道長期歡迎教育工作者來稿:email: nanzhouedu@sina
南方周末特約撰稿 蔣敏玉 南方周末記者 蘇有鵬